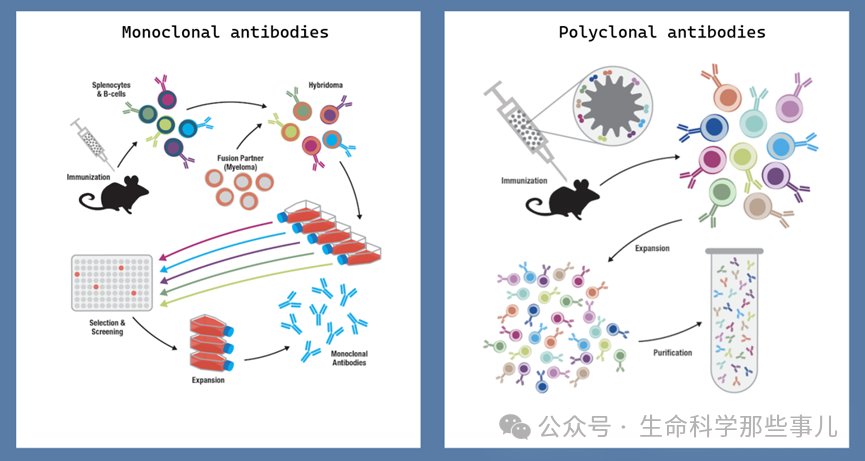文章来源公众号:VTALK 作者:vv
双有效载荷ADC进入首个肿瘤学临床试验
两种双有效载荷抗体-药物偶联物现已进入癌症临床,还有更多药物正在开发中。
“这个领域发生了很多事情,”双有效载荷初创公司 Callio Therapeutics 的首席战略官 Jerome Boyd-Kirkup 说。Callio 今年早些时候筹集了 1.87 亿美元来开发这些试剂,凸显了科学界和投资者对这项新兴技术的兴趣。总的来说,在该领域工作的公司在 4 月份的 AACR 会议上展示了十几个双有效载荷 ADC(表 1)。
Boyd-Kirkup 补充道,这些生物制剂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目前的 ADC——包括第一三共和阿斯利康最畅销的曲妥珠单抗 deruxtecan (Enhertu)——仍然有其局限性。并非所有癌症都对这些药物有反应,患者可能会很快复发。已经阻碍这些药物功效的耐药机制也可能削弱其使用相同弹头的实验性 ADC 的有效性。
一些药物开发商预计多种有效载荷 ADC 将打破这种僵局。“制药公司真正兴奋的是,双有效载荷 ADC 可以释放持久的功效,”双有效载荷 ADC 公司 CrossBridge Bio 的首席执行官 Michael Torres 说。“如果安全性可以被接受,那就是本垒打。”
然而,这项技术有很多尚待瞄准的靶标。与 ADC 一样,这些药物需要靶向在癌细胞上高表达的肿瘤抗原,而在健康细胞上尽可能少地表达。抗体和有效载荷之间的连接子需要进行微调。有效载荷需要很好地协同工作。整个ADC需要易于大规模制造。“你必须在这一切的每一个方面都深思熟虑,”托雷斯说。
Sutro 的首席战略官 Hans-Peter Gerber 补充道,不会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该公司自 2003 年以来一直在使用非天然氨基酸来制造生物制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抗体-连接子-有效载荷组合中的哪一种在哪些适应症中表现特别好,”他说。
因此,大型制药公司正在等待该技术进一步降低风险——目前该领域已经公开的公开的具有可行性的举措,大多数制药公司还保持着观望的态度”博伊德-柯库普说。
化疗+化疗组合
成都康宏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制药公司,已成为双有效载荷领域的快速先行者。
对于成都康宏生物制剂负责人赵永浩来说,当前ADC的临床数据积累凸显了对新方法的必要性。该模式在某些癌症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无进展生存数据,但患者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进展。
这当然是抗癌药物开发商面临的持续挑战。当快速生长的癌细胞用细胞毒性药物治疗时,它们会迅速拾取新的突变以逃避治疗效果——例如,激活替代信号通路,或上调药物外排泵,将药物清除出细胞。药物开发人员已经采用了组合策略来帮助关闭其中一些逃生路线,而 Zhao 将多有效载荷 ADC 视为一种通过单一治疗剂完成这一切的方法。
“我认为,为了克服耐药性,我们需要选择新的有效载荷,”赵说。
双有效载荷ADC领域的其他公司也持同样的想法。“如果你有两个有效载荷,肿瘤细胞必须找到围绕你抑制的每条通路发生突变的方法。细胞可能需要两倍的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格伯解释道。“在某些时候,你会超过可用于产生耐药突变的细胞数量。”
但是哪些有效载荷要配对在一起呢?
所有公开披露的程序都依赖拓扑异构酶 1 (TOP1) 抑制剂作为锚定剂。包括 exatecan 和 exatecan 衍生物 deruxtecan 在内的 TOP1 抑制剂已经在 ADC 社区中流行,通过对 DNA 复制机制造成麻烦来有效杀死快速循环的癌细胞。
在成都康宏,该团队选择将 exatecan 弹头与另一种抑制转录机制的化疗剂配对。他们将范围缩小到一种名为雷公藤内酯的 RNA 聚合酶 II 抑制剂,这是一种源自传统中药材“雷神藤”的天然产物。
赵说,做出这一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艾沙特康和雷公藤内酯的匹配纳摩尔效力。他说,ADC 的疗效、耐受性和最大耐受剂量取决于其最活跃有效载荷的效力,因此如果与超强效伙伴配对,低效药物可能不会提供太多治疗益处。
成都康宏的药物开发人员将这些有效载荷偶联到 TROP2 靶向抗体上。赵解释说,与 HER2 靶向 ADC 相比,sacituzumab govitecan (Trodelvy) 和 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roway) 等 TROP2 靶向 ADC 提供了更大的改进空间。他的团队将四个 exatecan 分子连接到抗体的臂上,平均将 3.5 个三醇内酯连接到茎上,总药物:抗体比 (DAR) 为 7.5。
他补充说,这些连接子在不同的时间被切割,以交错的方式释放有效载荷。exatecan 结合连接子更稳定,设计用于在 ADC 被目标癌细胞吸收以重击后被切割——尽管如果它被内体重新释放到更广泛的肿瘤微环境中,它也可以杀死附近的癌细胞。相比之下,雷公藤内酯连接子被设计为在 ADC 内化以取出周围癌细胞之前在肿瘤微环境中被切割,从而增强该药剂对更广泛的肿瘤组织的所谓旁观者效应。
在ADC到达肿瘤之前释放的任何雷公藤内酯都应具有最小的组织外毒性,因为该药物的半衰期仅为几分钟。相比之下,Exatecan 的半衰期为几个小时。“雷公藤内酯是 TOP1 抑制剂的一个非常好的有效载荷伙伴,”赵说。
临床前数据令人鼓舞,KH815 在各种耐药癌症模型中显示出活性。其中一项中,将对 sacituzumab govitecan 耐药患者的肿瘤细胞异种移植到小鼠体内,然后用 sacituzumab govitecan、datopotamab deruxtecan 或 KH815 退化。“我们的双有效载荷 ADC 具有抗肿瘤活性,但 sacituzumab govitecan 和 datopotamab deruxtecan 效果不佳,”赵说。
如果这些效应可以在人类身上复制,它们可以缓解人们对 ADC 领域交叉电阻模式日益增长的担忧。ADC 管道中的大多数药物使用 TOP1 抑制剂或微管蛋白抑制剂(如单甲基奥瑞他汀 E (MMAE))来杀死癌细胞。然而,一旦癌症对携带其中一种弹头的ADC产生耐药性,它通常也可以躲避相关弹头。随着 ADC 成为癌症护理标准的一部分,如果实验性单有效载荷 ADC 依赖已建立的弹头,它们将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成都康宏的小鼠数据表明,双有效载荷ADC可能会使肿瘤对他们以前见过的弹头重新敏感。
该公司目前正在招募患者参加 KH815 的试验。
总部位于中国的信达生物也在临床上推出了一种名为 IBI3020 的双有效载荷 ADC,靶向CEACAM5癌症抗原。然而,信达生物尚未披露ADC的弹头。
三重有效载荷也是如此
在 Araris,研究人员同样正在探索具有传统化疗有效载荷的 ADC——具有两种、三种或更多药物的组合。“当你看传统的化疗方法时,它总是关于联合治疗,”Arasis 的首席战略官 Philipp Spycher 说。“那么为什么不附加多个化疗有效载荷呢?”
Araris 的候选药物之一是一种 靶向 NaPi2b 的双有效载荷 ADC,携带两种相关的 TOP1 抑制剂:exatecan 和 exatecan 衍生物。阿拉里斯在旁观者活动方面也采取了深思熟虑的方法,但方向与成都康宏不同。在 Araris 的案例中,exatecan 在 ADC 内化和连接子裂解后从癌细胞中扩散出来,从而提供了大部分旁观者效应。同时,Araris 选择的 exatecan 衍生物具有低细胞通透性,因此会留在癌细胞内以增强靶向杀伤效果。
“我们希望有一个受控的旁观者活动,这可以让我们真正最大限度地提高效力和耐受性,”Spycher 说。“我们具有相当高的活性和体内耐受性,”他补充道。
Araris 的另一个候选药物是一种三有效载荷 ADC,它用两种 TOP1 抑制剂和微管蛋白抑制剂 MMAE 靶向表达 Nectin-4 的细胞。“这两种有效载荷类别都针对 Nectin-4 进行了很好的验证,”Spycher 说。
他补充说,MMAE 似乎会触发免疫原性形式的细胞死亡,从而增加了这种 ADC 与免疫增强检查点抑制剂良好配对的几率。
至少还有四家公司也在将 TOP1 抑制剂与微管蛋白抑制剂相结合——这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两种 ADC 有效载荷。“有时你不应该想太多,”Gerber 说,他在 Sutro 的团队也在探索这种方法。他补充说,关键是一起测试有效载荷,看看会发生什么。
但其他人警告说,只关注最流行的弹头可能会带来问题。Boyd-Kirkup 说,已经对第一种 TOP1 抑制剂产生耐药性的癌细胞也可能对第二种 TOP1 抑制剂产生耐药性。赵补充道,由于 MMAE 比 exatecan 更有效,因此 MMAE 本身可以定义由此产生的 ADC 的治疗潜力和耐受性。
其他因素也可能对这些配对产生影响。“我们自己研究了 TOP1 加微管蛋白抑制剂,”托雷斯说。“在一些细胞系中,我们看到的是效果拮抗作用,而不是协同作用。”
然而,对于 Spycher 来说,TOP1 和 MMAE 的组合为 Araris 的连接器技术提供了大放异彩的机会。
Araris 的连接子由支链肽组成,所有有效载荷分子通过单个连接子连接到抗体上的单个谷氨酰胺上。“我们希望生成稳定的 ADC,一方面又像没有连接有效载荷一样,”Spycher 说。他解释说,连接子被设计为足够亲水,可以掩盖其有效载荷的疏水性,这有助于避免 ADC 被非特异性摄取到非癌组织中。它经过优化,使其在内化到癌细胞中时不会立即被切割。
“我们的有效载荷释放得相当缓慢,”他说。“我们认为这是秘诀的一部分”。
今年早些时候,大冢的子公司 Taiho 斥资 4 亿美元收购了 Araris 及其连接器技术。Araris 领先的单有效载荷项目正在采用 FDA 批准的靶向 CD79b 的 polatuzumab vedotin (Polivy),该药物采用 Araris 的偶联和连接子技术来代替 polatuzumab vedotin 中使用的技术。
“我们想证明,通过我们的连接器技术,我们可以进入 polatuzumab vedotin 失败的适应症,”Spycher 说。他补充说,如果单独使用连接子就能提高单有效载荷 ADC 的治疗指数,这也预示着它在多有效载荷环境中的前景。
TOP1 和微管蛋白抑制剂组合的另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使 DAR 恰到好处,也许比 MMAE 加载更多的 exatecan 在抗体中。在 Sutro,该团队迄今为止已经尝试了包括 6+2、8+2 和 8+4 在内的 DAR。“我们手头有工具来微调双有效载荷组合,以获得最大的治疗指数,”Gerber 说。“获胜的 ADC 将是两个有效载荷之间具有正确比例的 ADC。”
Sutro 最近在 PEGS 2025 上展示了临床前数据,表明 TOP1 和 MMAE 组合也可以使癌症对 ADC 重新敏感。Sutro 通过用 TOP1-ADC 曲妥珠单抗 deruxtecan 治疗异种移植小鼠直到肿瘤产生耐药性,然后用载有微管蛋白抑制剂半甾林的 ADC 治疗小鼠,直到它们再次产生耐药性,从而制作了耐药模型。然后,他们用基于 TOP1 和 MMAE 的双有效载荷 ADC 治疗小鼠。
“肿瘤再次消退,一直往下,”格伯说。“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诊所会发生什么。
推动有效负载
其他人正在进军图表较少的有效载荷领域,希望更具战略性的药物-药物组合可能会提供更好的效果。特别是破坏 DNA 损伤反应 (DDR) 的药物可以与 TOP1 抑制剂很好地结合使用。
Boyd-Kirkup 补充道,癌症基因组数据支持了这一点。他说,癌症可以通过上调 DDR 基因来产生对 TOP1 抑制剂的耐药性,从而实现 DNA 损伤修复。相反,合成致死率数据库表明,对 DDR 基因的扰动使细胞特别容易受到 TOP1 抑制。“从科学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他补充道。“DDR 是细胞激活以减弱这些细胞毒性作用的途径之一。”
经验有效载荷筛选数据也具有支持性。“我们生成的数据确实表明,TOP1 抑制剂与 DNA 损伤修复抑制剂的组合将非常有效,并且将解决我们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看到的耐药机制,”Boyd-Kirkup 说。
ATR 是 DDR 的主要调节器,位于这个合成杀伤力的最佳点。Boyd-Kirkup 解释说,肿瘤细胞已经对 ATR 抑制高度敏感,而没有充满癌症突变且未暴露于 TOP1 抑制的健康细胞应该更具弹性。“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将有一个更广阔的治疗窗口,”他说。
该团队的 HER2 靶向 CLIO-8221(以前称为 HMBD-802)将 TOP1 抑制剂与 ATR 抑制剂相结合,DAR 为 4+4。到目前为止,当在 NHP 中以高剂量使用时,他们还没有发现这种方法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协同毒性。Callio 计划在 2026 年第一季度之前为第一位患者注射 CLIO-8221。
CLIO-8221 的一个机会是用于 HER2 表达水平较低的癌症,这些癌症通常对 HER2 靶向 ADC 的反应不佳。Boyd-Kirkup 补充道,在这些癌症中的成功可能表明,双有效载荷 ADC 对于其他低表达水平的癌症相关抗原来说是一种可行的策略,这些抗原迄今为止已被证明对 ADC 有顽固性。
CrossBridge Bio 的研究人员还专注于 TOP1 加 ATR 抑制双有效载荷 ADC。“我们进行了不同浓度的免费有效载荷筛选和涵盖 DDR 领域的药物矩阵,我们着陆的地方是我们看到最大协同作用的地方,”Torres 说。
当谈到双有效载荷 ADC(以及更普遍的抗癌药物开发)时,研究人员仍在等待可靠的临床数据,证明组合可以提供协同而不是附加益处。但对于托雷斯来说,临床前数据表明一加一可能大于二。“在这方面,我们有非常好的新兴数据,”托雷斯说。
今年晚些时候,该公司计划展示其中一些数据。在他们将展示的一种体内癌症模型中,小鼠被处理为 datopotamab deruxtecan 作为基准 ADC、使用 CrossBridge Bio 的分支连接子技术构建的单有效载荷 ADC 或该公司的双有效载荷 ADC 之一。Torres 说,没有一只小鼠对基准测试代理做出反应,只有一半对单有效载荷 ADC 做出反应,但它们都对双有效载荷 ADC 做出了反应——并且在 120 天内继续这样做。
“这就是制药公司真正兴奋的地方,”他说。
Sutro 也在试验 TOP1 抑制剂与 DDR 抑制剂联合使用,但尚未披露具体目标或有效载荷。然而,在 AACR 上,他们表明 DNA 损伤传感器蛋白 PARP 的抑制剂可以增强 TOP1 抑制剂的作用。
“总的来说,我们正在研究 DNA 双链修复抑制剂,”格伯说。
免疫激活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双有效载荷 ADC 将细胞毒素与免疫系统刺激剂结合起来,以期让免疫系统参与进来更好地杀死癌症。诺华和塔拉克治疗公司等公司的药物开发商已经用免疫刺激剂标记了抗体,试图从抗体中获得更好的免疫治疗效果,但目前还没有明显的临床胜利。免疫刺激双有效载荷ADC旨在将这一概念更进一步。
Gerber 说,免疫疗法和 ADC 非常适合彼此。他解释说,免疫疗法具有持久的效果,但对较大肿瘤的疗效有限。相比之下,ADC 非常适合减瘤,但不可避免地会被耐药机制所中和。“如果你将两者结合起来,你能做的就是减少肿瘤的体积,以便免疫激动剂可以激活免疫系统,”他补充道。
“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概念,”格伯说。
Sutro 与安斯泰来合作开发了两款双有效载荷免疫刺激 ADC (iADC),其中一款目前正在进行 IND 毒理学研究。它尚未透露它优先考虑哪些靶点或免疫激动剂。
临床数据传入
随着两个双有效载荷 ADC 现在在临床上,研究人员很快就会看到这些药物在人类中的表现如何。与往常一样,第一阶段数据的最大问题将是安全。
“这些双有效载荷是否足够好地协同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剂量水平前进,并且仍然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安全的药物?”虽然科学文献中充斥着杀死培养皿或小鼠中肿瘤细胞的 ADC,但这些药物中很少有具有进入人体所需的治疗窗口。“这就是我所关注的,”他说。
有效载荷相关的毒性可能因方案而异。以成都康宏的 KH815 为例,exatecan 会导致血液学毒性,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雷公藤内酯也具有血液学毒性。那么这些毒性会叠加吗?
“如果这两种药物都会导致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或类似的东西,它们会相互加剧吗,”托雷斯问道。“安全将是一个重要的读数。”
应答率和应答持续时间也是关注重点。但托雷斯补充道,这些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失误可能几乎无法理解更广阔的领域。不同的双有效载荷ADC在目标、有效载荷和指示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即使是对连接器的细微变化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你没有一个干净利落的连接剂,那将是灾难的根源。”
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公司已经采用了各种不同的链接策略。虽然 Callio 和 CrossBridge 正在研究分支连接子共轭策略,但 Sutro 和成都康宏正在为不同的有效载荷使用不同的连接子。Araris 结合使用了这两种方法。Gerber 说,不同的连接子策略将为每个双有效载荷 ADC 赋予独特的特性、裂解曲线和可制造性卖点,这些可以决定候选产品的成败。
“对于概念验证,任何不同的共轭技术都可以,”他补充道。“看到这将如何在临床上发挥作用,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